中国艺术的生命理想:四众香界
朱良志
王昌龄《题僧房》说:“棕榈花满院,苔藓入闲房。彼此名言绝,空中闻异香。”
李白《庐山东林寺夜怀》说:“天香生虚空,天乐鸣不歇。宴坐寂不动,大千入毫发。”
两位诗人所说的天香、异香,都是佛的境界。最后我想借用佛教中香的境界,谈谈中国艺术的生命理想问题。
禅宗中经常有香象渡河这样的话头,此出于佛经。佛经上说,兔子、马和香象三种动物一起渡河,兔子渡河是浮在水面上,比喻那些对佛法一知半解的人,马渡河半个身子在水里,半个身子漂在水上,比喻那些半吊子的学法人。而香象渡河,因为体积大,一下就堵住了河流。这比喻那些深悟佛法的人。为什么是香象呢?在印度,香象是正处在发情期的象,它力大无比,充满吸引力。禅宗用它来比喻悟禅的道理,有三条:一是截断众流,当下直接;二是比喻信心,深深的影响力,一个悟者对他者具有熏染的能力,香风四溢。三是精进之力,能此悟,无所不能。诗家常常借此来形容诗之悟。
佛教中的最高境界被称为香国或者“众香界”,这是一个充满香的世界,在那高高的须弥山顶,有国名众香,有佛名香积。它所传出的香气,传遍了宇宙。《维摩诘经》有《香积佛品》,说的就是这个香世界。在这个香的世界中,一切都散发出浓浓的香气,以香作楼阁,人所经过的地方都有鲜花点缀,香气扑鼻,诸天中下着香花雨,天女在散着花,须弥山充满了香味,就连车轮也是花所做成,苑园的物品都用香料熏染,殿堂里香烟缭绕,而其中的菩萨就叫香积菩萨,他们所吃的食物也香气四溢,周流十方世界。所谓香积菩萨的意思,取的就是积聚天下众香的功德。而来此修行的人,要染香水,吃香饭,并谈着香的语言,呼吸着香的气息,每个修行人的毛孔中都散发出香气。他们简直是一批香人。维摩诘化作菩萨,到众香界,礼拜香积菩萨,香积菩萨以众香钵,盛满香饭,与化菩萨。维摩诘用这香饭普熏毗耶离城,其影响及三千大千世界,无数的人感受他的香气。
佛教的天国就是这样的香世界,佛所传的道理就是香气四溢的大道理,对佛的信仰者就是香客。佛祖拈花,迦叶微笑,一花开五叶,一念心清净,处处莲花开,等等,都在强调一种理想的境界,强调人类应秉持一种不染之心。如同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,清净微妙。正如孟浩然在《题大禹寺义公禅房》中所说的:“夕阳连雨足,空翠落庭阴。看取莲花净,应知不染心。”
在禅宗中,到处洋溢着这香气。如牛头法融修行之时,传百鸟衔花来供养他。有一位禅师上堂说法道:“千般说,万般喻,只要教君早回去。去何处?”过了一会,他说:“夜来风起满庭香,吹落桃花三五树。”回到生命的本然,回到那散发着生命香味的地方。后世的丛林都以香气缭绕为其重要特点。“拥毳对芳丛,由来趣不同。发从今日白,花是去年红。艳冶随朝露,馨香逐晚风。何须待零落,然后始知空”;“常忆江南三月里,鹧鸪啼处百花香”;“锦绣银香囊,风吹满路香”,等等,禅是一个香世界。
佛以香来象征最高信仰世界,因为香在这里代表的是人的精神追求,是渴望,是在水一方的期许;悟入香的世界的主要意思,就是远离污秽。因为在佛教看来,尘世间充满了污秽,人的排泄物、人的离去、人的气味,污浊得令人窒息。污秽更染污了人的精神。佛提供了远离这一污秽的道路。同时,佛教中香的象征还在于,香是一种信心,一种发自心底的力量,那是人的生命的本源力量,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这种力量。佛要将这力量引出。中国艺术的冷香逸韵,正是要护持这样的力量,簇拥着这样的理想。
明画家李日华题画诗道:“霜落蒹葭水国寒,浪花云影上渔竿。画成未拟将人去,茶熟香温且自看。”就以清净的心去饮一杯香茶吧,在那香雾腾起处,也许能听到生命的妙音。
 静中求飞
静中求飞
南宋词人、音乐家姜白石一次客武陵(湖南常德),发现一片阒寂而迷人的地方,这里野水迢递,乔木参天,人迹罕至,最突出的是一片弥望无际的荷塘,荷叶田田,清香四溢,微风徐来,远远看那荷塘如绿云飘渺,偶尔一阵响动,忽见荷叶间一闪而过的船影。白石有感此境,写下了这首《念奴娇》词:
闹红一舸,记来时、尝与鸳鸯为侣。三十六陂人未到,水佩风裳无数。翠叶吹凉,玉容销酒,更洒菰蒲雨。嫣然摇动,冷香飞上诗句。 日暮。青盖亭亭,情人不见,争忍凌波去。只恐舞衣寒易落,愁入西风南浦。高柳垂阴,老鱼吹浪,留我花间住。田田多少,几回沙际归路。
这是一首咏物杰作,将荷塘的冷香逸韵和思人联系起来,构思别致,对荷花荷叶的描写极生动传神。黄昏下,词人的心在荷塘中荡漾。那赏荷的船只(闹红一舸),其实也在他的心中搅动。这首词给我强烈的感觉,是一个“舞”字。
我将这出《荷韵》之舞戏分为四个段落:
开始,无数荷花衬着荷叶在微风中跳着率意的舞蹈,拉开这薄暮荷舞的序幕;
接下来是悠然的享受,如同舞者从容地旋转,翠绿的叶儿洒着一串串珠圆玉润的水滴,在飞离,飞离,嫣然摇动所涌起的冷香逸韵飞向了诗心笔底。
再接下是盘桓,日暮沉沉,但见得荷叶亭亭,像一个个等候游子的佳人,怕只怕寒来翩翩舞衣衰落,随西风,一腔愁怨化南浦。这是舞者执意的流连。
最后一幕更为动人,高柳垂下绿阴,老鱼跳起波浪,都像是要请观者留步花间,但观者已去,在沙洲归路上还在想,荷叶不知留下多少?舞影稍歇,余韵未了。
在我看来,这不是平凡的荷舞,它舞动的是艺术家的芳心。
舞可以说是中国艺术的精魂。宗白华先生曾说,中国艺术的最高形式是书法,书法的根本精神在乐,而乐是伴着音乐的节奏在跳舞。高妙的书法,就是一个个舞者。南朝宋宗炳好山水,晚年病足,不能远行,画山水张之于壁,以尽卧游之乐。他常常对人说:“抚琴动操,欲令众山皆响。”群山都伴着音乐的节奏跳起了率意的舞。好的书法,就给人这样的感觉。
我国上古时期诗、乐、舞是不分的。诗以道其志,乐以和其声,舞以动其容。诗之不足,故咏歌之,咏歌之不足,不知手之舞之,足之蹈之。舞是发自生命深层的自觉力量。在后来中国艺术的发展中,舞的精神穿透了艺术的寂寞世界,让生命舞起来,让自己获得支配生命的力量,成为天地间的强音。艺术家将内在精神的跃动,通过舞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。中国艺术有所谓“剑器箫心”的说法,龚自珍就曾以“兼得于亦剑亦箫之美”,为最高的心灵境界。箫是音乐,剑则是舞蹈。
舞的精神贯穿中国艺术,有两个重要原因,一是中国哲学强调以静制动,在宁静中表现活泼泼的生命精神,一阴一阳之谓道,是中国艺术的精魂,阴阳互动,舒卷自如,即是舞了;二是中国艺术有重视线条的倾向(即使在非造型艺术中,重视线条的精神也不可忽视),舞的精神即在线条的律动。
舞的精神在中国艺术中,体现为动静相参的思想,动中有静,静中有动,动静相宜。我这一讲,就是以舞为契机,通过具体艺术活动的解释,谈谈中国艺术理论中动静相参的学说。
 一 静中求飞
一 静中求飞
稳如泰山,飞如流云,这是静穆中的飞动。以动追动,不为高明,必于静中追动,这样的飞动,才能真正感人。寂然不动,感而遂通,才有艺术的高致。在中国艺术中,这样的动,似静而实动:表面上宁静如水,实际里暗含旋涡。
唐代艺术史上有一个美妙的传说,就是所谓吴道子作画、张旭作书、裴旻(mín)舞剑的“三绝”说。朱景玄《唐朝名画记》记载:
吴道玄,字道子,东京阳翟人也。少孤贫,天授之性,年未弱冠,穷丹青之妙。浪迹东洛,时明皇知其名,召入内供奉。开元中,驾幸东洛。吴生与裴旻将军、张旭长史相遇,各陈其能。时将军裴旻厚以金帛,召致道子于东都天宫寺,为其所亲将施绘事。道子封还金帛,一无所受。谓旻曰:“闻裴将军旧矣。为舞剑一曲,足以当惠,观其壮气,可助挥毫。”旻因墨缞为道子舞剑。舞毕,奋笔俄顷而成,有若神助,尤为冠绝。道子亦亲为设色。其画在寺之西庑。又张旭长史亦书一壁。都邑士庶皆云:“一日之中,获睹三绝。”
此三绝乃是书画舞的会通,三绝成一圣艺,成就那飞动的心灵。观其壮气,可助挥毫,化剑的舞影为书画飞动的笔致。
画是静止的,吴道子知道,静不是艺术追求的目标,艺术形式需要有活的韵味。他要借剑舞启动自己蛰伏的心灵,活跃自己僵滞的笔致,进而神超形越。传他曾在内殿墙壁上画五条龙,龙的鳞甲飞动,简直能令苍天欲雨,大地生烟。吴道子的人物画也能在宁静中传飞动之势,衣纹飘飘而举,优柔回环,别具一种面貌。苏轼称赞他的艺术: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,寄妙理于豪放之外。”道子的画笔势圆转,衣服宽松,裙带飘举,用运动感较强的莼菜条,而且多用白描手法,正是“吴带当风”的感觉。传为他所作的《送子天王图》,就是如此。米芾《画史》说他“早年行笔言细,中年行笔磊落,挥霍如莼菜条。人物有八面,生意活动,方圆平正。高下曲直,折算停分,莫不如意。其传彩行焦墨痕中。略施微染,自然超出缣素,世谓之吴带当风”。吴道子飞动的线条,有一种超越的精神。
唐代艺术史中有关于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而作书的美妙传说。“昔有佳人公孙氏,一舞剑器动四方。观者如山色沮丧,天地为之久低昂。”杜甫对公孙大娘剑势有这样的描绘,今天我们无法知道这位女舞蹈家的具体形象,但从张旭的《古诗四帖》中,似乎还能揣摩公孙大娘的剑意。
前人评王羲之书法“飘若游云,矫若惊龙”,这也可以说是对中国书法精神的揭示。云飞龙跃的舞动,表达了中国书法对活泼生命精神的追求。王羲之的飞动,正是在静穆中求得的,如我们看他的《快雪时晴帖》,就能深切体会到这种精神。
书法最忌静,一味静,则呆滞,呆滞则无生气,无生气,即无韵味。故在书法中,宁静中追求飞动的韵律,演成含蓄的生命舞蹈,最为书家所重。中国书法的节奏如鹰击长空、飞鸟出林、秋蛇出洞、飞龙翔天……墨线翻飞中完成生命的狂舞。
翻开古代书论,满目“飞动”二字。蔡邕《笔论》:“为书之体,须入其形,若坐若行,若飞若动,若往若来,若卧若起,若愁若喜,若虫食木叶,若利剑长戈,若强弓硬矢,若水火,若云雾,若日月。”他在《篆势》中说篆字的妙处在“若行若飞”。晋卫恒在《四体书势》中说:“远而望之,若飞龙在天。”唐窦蒙《述书赋》列“飞”“动”二格,所谓“若灭若没曰飞”,“若欲奔飞曰动”。唐蔡希综《法书论》说:“每字皆须骨气雄强,爽爽然有飞动之态。”宋黄伯思《东观余论》也说:“及造微洞妙,则出没飞动,神会意得。”类似这样的论述很多。
飞动,成为品评书法的主要标准,如蔡希综评张旭书法:“群象自动,有若飞动。”《宣和书谱》评怀素“字字飞动,圆转之妙,宛若有神”。米芾论书,也强调“飞动气势”,认为达到飞动,也就有了“逸韵”。飞动,不光是对草书、行书的要求,也是中国书法所有书体必须遵循的原则。张怀瓘评李斯篆书:“画如铁石,字若飞动。”明汤临初说:“点画、使转,皆笔也,成此点画、使转,皆用笔也。小而偏旁,大而全体,有顺利以导,而天机流荡,生意蔚然,有反衄(nǜ)以成,而气力委婉,精神横溢。顺之不类蛇蚓,逆之不作生柴,方书而形神俱融,成字而飞动自在,此造化之工,鬼神之秘也。”有了飞动,就有了“天机流荡、生意蔚然”的韵味。清人宋曹总结书法要则时说:“无非要生动,要脱化。”
书法是空间艺术,但传统书论更强调它的时间性,要在空间中体现出时间的节奏,使抽象的线条展示出生命变化的趣味来。看汉碑名品《石门颂》,你能明显感到在肃穆的形式中包含着飞翔的意味。此书有“隶中草书”之称,正因其于极静中追求至动,所以给人野鹤闲云的感觉。当代书法家萧娴说此帖有“武士挥戈,气势逼人”的境界。我感到此帖是端坐中的飞动,如一“受”字,起首一横挑,透力万钧,结末处一掠一波,使人如听到书写时的涩动之声。
又如《爨宝子》碑,此碑刻于东晋大亨四年(405),与《爨龙颜碑》合称为云南“二爨”。书为隶书,但也杂有草意,如《张迁碑》一样,以方笔运笔,结体方正古板,呈肃穆之态。但却在肃穆之中有飞动之势。康有为说此碑有“端朴若古佛之容”。我觉得,此帖笔画如累石,有参差嶙峋之美感,别具风裁。笔势内敛,不伸展,有自在回旋之势。
又如汉《礼器碑》,此碑作于汉永寿二年(156),扁笔运笔,笔细横平,显稳定之态,是汉碑中法度谨严的代表作品。但扁中有挑,尖锋挑出笔外,人称“燕尾”。横中有曲,显飞动之姿,而细中有粗,捺脚粗出。翁方纲以为此碑为汉隶第一。此碑的字体铁画银钩,细而不弱,平和从容,极尽俯仰之态。
中国的建筑艺术也追求飞动之势。如被称为“燕尾”的飞檐最是典型,使得静止的体态中有燕舞飞花之妙。《诗经·小雅》中的《斯干》篇,描写周宣王筑宗庙的情景,其中说到宗庙的建筑,就用“如跂斯翼,如矢斯棘,如鸟斯革,如翚斯飞”来形容其特点--有的如人耸立张开双手,有的如人举箭奋力拉弓,有的如鸟张其两翼待飞,有的如鸟儿展翅高扬。在今天所见到的有浓厚民族风格的建筑中,这样的例子实在太普遍了。
我们在篆刻中也能感到这种飞动之势。中国印学是追求活力的,何震说“章法要整齐,更要活泼”,他的印如闲云舒卷,运转自如。朱简《印经》说:“行行有活法,字字有生动。”秦爨公赞甘旸章法“刀法老而有生趣”。赵凡夫《印学指南》述印之四品,也重飞动之韵,他说:“法由我出,不由法出,信手拈来,头头是道,如飞天仙人偶游下界者,逸品也。体备诸法,错综变化,莫可端倪,如生龙活虎捉摸不定者,神品也。非法不行,奇正迭运,斐然成文,如万花春谷灿烂夺目者,妙品也。”而只知道刻镂形似印作,没有飞动之趣,只能算能品。
如清代篆刻家徐三庚,其印有“吴带当风”之评,在辛辣中透出飘逸之态。这里所举的五印,很有风味。“烟云室”,自得飞腾云间之妙。“一园水竹权为主”,真有雍容为主之姿,我就是这园中的主人,我的心灵与园中众景共俯仰。而“临窗一日几回看”,真能使人有“决眦看飞鸟”的感受;而“写心”,如水之流,倾泻着内在世界。其中在构图上,我最爱“久盦”一方,表现了跪拜生命的意思。
 二 飞中求挫
二 飞中求挫
一股强大的力向前飞动,如骏马从千丈坡上往下冲去,突然之间猛勒马首,骤然停住,马踏原地,低首嘶鸣,强大的力感收于其中。又如奔腾而下的激流突然遇到巨石当前,猛然转折,激起千堆白雪。中国艺术追求“狡兔暴骇,将奔未突”的美感,那是未发前对力的凝聚,而这是已发后对力的收摄,是划然而至的休止符。这是强调飞动的中国艺术的更深一层意韵,也是中国美学所推崇的“顿挫”的美感。中国艺术的形式空间,是一回荡的世界。
东汉蔡邕言书法之妙,得二字,一为疾,一为涩。据冯武《书法正传》载:“邕尝居一室,不寐,恍然见一客,厥状甚异,授以九势,言讫而没。邕女琰,字文姬,述其说曰:‘臣父造八分时,神授笔法曰:书肇于自然,自然既立,阴阳生焉;阴阳既生,形气立矣。藏头护尾,力在其中,下笔用力,献酹之丽。故曰:势来不可止,势去不可遏。书有二法,一曰疾,二曰涩。得疾涩二法,书妙尽矣。夫书禀乎人性,疾者不可使之令徐,徐者不可使之令疾……’”这个故事当然是后人编的,但表现的意思却是明确的。
疾和涩,是中国书法美学中一对关键的概念。王羲之在《记白云先生书诀》中提出:“势疾则涩。”就是要于疾中求涩,在飞动中求顿挫,在疾和涩二者之间寻求最大的张力。刘熙载云:“古人论书法,不外疾涩二字。涩非迟也,疾非速也。”他将古代书论之秘密,就概括成这两个字。
我想先通过一些语言艺术来把玩它的独有魅力。
昆明有大观楼,大观楼上有一副对联,号称中国最长的对联,其云:
五百里滇池,奔来眼底。披襟岸帻,喜茫茫空阔无边。看东骧神骏,西翥灵仪,北走蜿蜒,南翔缟素,高人韵士,何妨选胜登临,趁蟹屿螺洲,梳裹就风鬟雾鬓,更蘋天苇地,点缀些翠羽丹霞。莫辜负,四周香稻,万顷晴沙,九夏芙蓉,三春杨柳。
数千年往事,注到心头。把酒凌虚,叹滚滚英雄谁在。想汉习楼船,唐标铁柱,宋挥玉斧,元跨革囊,伟烈丰功,费尽移山心力,尽珠帘画栋,卷不及暮雨朝云,便断碣残碑,都付与苍烟落照。只赢得,几杵疏钟,半江渔火,两行秋雁,一枕清霜。①
上下联风味各别,上联以飞驰的节奏,数点五百里滇池之美,真有“一夜看遍长安花”的气势,烟云风暴,浩浩汤汤,有四周香稻,万顷晴沙,九夏芙蓉,三春杨柳,几乎是如数家珍,要一口说尽江山风景,有神骏飞舞之妙。而下联话锋突转,由景及史,茫茫历史,都付与苍烟落照,几声怅惘,一行清泪,由上片飞腾的气势,发而为生命的哀惋。上联节奏快,下联节奏慢;上联有飞势,下联有挽力;上联是放,下联是收;上联在痛快,下联在沉着……真是收放自如,沉着痛快。高扬的气势和落寞的忧伤,参差错落,别具一番情愫。
类似这副对联的节奏在中国艺术中非常普遍,这里以元曲为例,稍加延伸。
白朴《庆东原》云:“忘忧草,含笑花,劝君闻早冠宜挂。那里也能言陆贾,那里也良谋子牙。那里也豪气张华?千古是非心,一夕渔樵话。”短短的小曲中,有顿挫的节奏。
陈草庵《山坡羊》说:“晨鸡初叫,昏鸦争噪。那个不去红尘闹?路迢迢,水迢迢,功名尽在长安道。今日少年明日老,山,依旧好;人,憔悴了。”气势排荡,突然收摄,令人心悸神摇,不能已已。
元好问《骤雨打新荷》是一首极负盛名的作品,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说:“至元代,如《骤雨打新荷》之类,则愈出愈新,不拘字数,填以工尺。”其云:“绿叶阴浓,遍池塘水阁,偏趁凉多。海榴初绽,妖艳喷香罗。老燕携雏弄语,有高柳鸣蝉相和。骤雨过,珍珠乱糁,打遍新荷。 人生有几?念良辰美景、一梦初过。穷通前定,何用苦张罗。命友邀宾玩赏,对芳樽浅酌低歌。且酩酊,任他两轮日月,来往如梭。”一场骤雨过后,空气清新,新荷乍露,亭亭玉立,柔雨打过,但见得珠圆玉润,煞是可爱。上半部分突出时令物征,下半部分由景物联系到人生的感叹。声韵和美,不事雕琢。
中国艺术论将此称为“沉着痛快”的美感。严羽曾总结唐诗的风格之妙有二:一是优游不迫,一是沉着痛快。像杜诗就属于沉着痛快一类。如其名作《登岳阳楼》:
昔闻洞庭水,今上岳阳楼。吴楚东南坼,乾坤日夜浮。亲朋无一字,老病有孤舟。戎马关山北,凭轩涕泗流。
大历三年之后,杜甫出峡漂泊两湖途中曾登岳阳楼,此诗即作于这次登临中。明批评家胡应麟曾以此诗为“盛唐第一”,此诗将“沉郁顿挫”的风格发挥到了极致。前四句登楼所见,拉开了浩大无边的景观,浩淼的湖水将吴楚东南分开,浩浩的天地就好像日夜在湖面漂浮。风格昂厉。后四句突音转调换,格调幽咽,怆然含悲。前后大开大收,有一种顿挫回环之美。
清人陈廷焯论词提倡“沉郁顿挫”,他说:“顿挫则有姿态,沉郁则极深厚。既有姿态,又极深厚,词中三昧亦尽于此矣。”如其评辛弃疾词云:“稼轩‘更能消几番风雨’一章,词意殊怨。然姿态飞动,极沉郁顿挫之致。起处‘更能消’三字,是从千回万转后倒折出来,真是有力如虎。”
该词为:
更能消、几番风雨,匆匆春又归去。惜春长怕花开早,何况落红无数。春且住!见说道、天涯芳草无归路。怨春不语,算只有殷勤,画檐蛛网,尽日惹飞絮。 长门事,准拟佳期又误,蛾眉曾有人妒。千金纵买相如赋,脉脉此情谁诉?君莫舞!君不见、玉环飞燕皆尘土。闲愁最苦,休去倚危阑,斜阳正在,烟柳断肠处。
--(《摸鱼儿》)
所谓“姿态飞动,极沉郁顿挫之致”,诚为的评,在飞动中见沉郁之妙,这的确是稼轩的妙处。我倒觉得他的《水龙吟·登建康赏心亭》更具此一势态:
楚天千里清秋,水随天去秋无际。遥岑远目,献愁供恨,玉簪螺髻。落日楼头,断鸿声里,江南游子,把吴钩看了,阑干拍遍,无人会、登临意。 休说鲈鱼堪烩,尽西风,季鹰归未?求田问舍,怕应羞见,刘郎才气。可惜流年,忧愁风雨,树犹如此。倩何人唤取,红巾翠袖,揾英雄泪?①
这首词比较难懂,为助理解,试译如下:秋高气爽楚天千里一片空阔,江水流向天边去,漫漫秋色无际,眺望北国崇山峻岭,如同美人头上的螺髻,把无边的愁陈说。就在这落日楼头、断鸿声里,一位江南游子,低头细看吴钩宝刀,拍遍了栏杆,但无人解会他登临之意。不要说西风起秋天到鲈鱼又上市,张季鹰受此诱惑,辞官回乡了吗?如果像许汜那样求田置屋,怕也羞见风流倜傥的刘备。可惜时光流转,风雨飘摇更使人忧愁。桓温的“树犹如此”的感叹时时从胸中涌起。此情此景,只有请人唤少女前来,用她那红巾翠袖,拭英雄泪。
这首名作为登楼所叹,用语奇警,豪放沉雄,尤其是“把吴钩看了,阑干拍遍,无人会,登临意”,如雄狮被困,极为感人。吴文英有词云:“落叶霞飘,败窗风咽,暮色凄凉深院。瘦不关秋,泪缘生别,情锁鬓霜千点,怅翠冷搔头燕,那能语恩怨。”这个“败窗风咽”,正是此境。
《二十四诗品》有《沉著》一品,其云:“绿杉野屋,落日气清。脱巾独步,时闻鸟声。鸿雁不来,之子远行。所思不远,若为平生。海风碧云,夜渚月明。如有佳语,大河前横。”
此品要在深沉厚重,气韵沉雄。得沉着之韵,必痛快,必凝重,实实在在,爽爽快快。飞动中含凝滞,越凝滞越飞动。一个隐逸者,脱巾披发,独步山林,偶尔听到一两声鸟鸣,更觉得山静气清。此写幽人山居的潇洒无羁,沉着痛快。虽然所思之人远行他方,但此刻在这寂静的山林里,思之转深,思之愈切,思之思之,所思之人好像来到眼前,正在对他诉说自己的境遇。如此清风明月夜,耳听海涛阵阵,仰望一丸冷月高悬,尘襟涤尽,世虑都无,心语如骏马奔腾而出。然骏马前驰,但见得一条大河前横。正是痛快中有凝滞,飞动中见涩转。
齐白石的很多印章具有这种特点。齐白石主张篆刻“快剑断蛟”、“昆刀截玉”,他多采用单刀侧锋直入的方法,线条刻削,若刀斧所砍,一面光洁一面毛糙,有纵横排奡(áo)之气。他的印章在构图上大开大合,妙处在收的关节,末笔多控。真有些“败窗风咽”的意味。如“宝辰”的结体,上密下疏,收意极明。如“悔鸟堂”中“堂”字的最下两横,侧刀嵌入,仪态万方。用他印章中的“花未全开月未圆”评价他的印风,倒很恰当。
白石印风的妙处,就在一个“勒”字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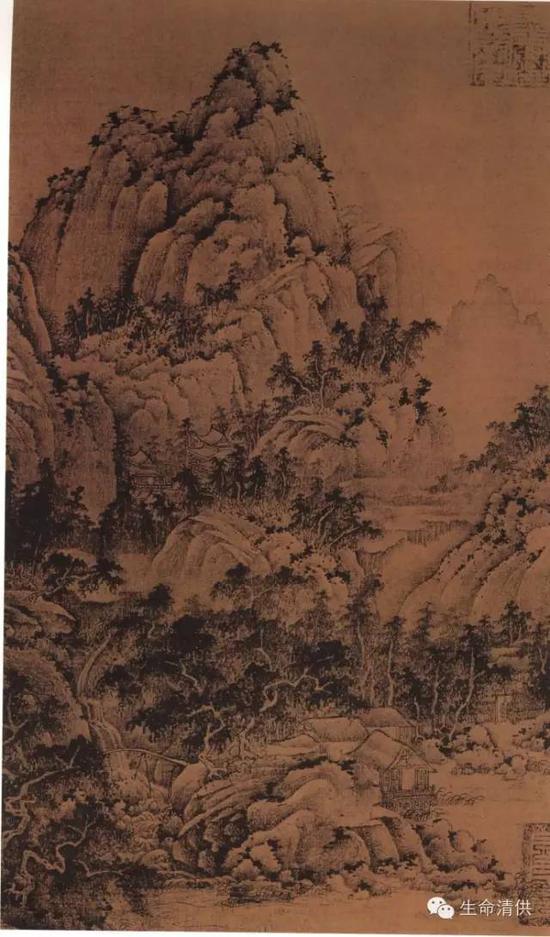 三 常中求醉
三 常中求醉
清刘熙载说:“诗善醉,文善醒。”
怀素说他的书法:“醉来信手两三行,醒来却书书不得。”
我以为,“花间一壶酒”可以说是中国艺术的一个象征,花间是艺术,酒影中有一个艺术的创造者。此出于李白《月下独酌》。诗云:“花间一壶酒,独酌无相亲。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。月既不解饮,影徒随我身。暂伴月将影,行乐须及春。我歌月徘徊,我舞影零乱。醒时同交欢,醉后各分散。永结无情游,相期邈云汉。”诗的大意是:花丛中摆上一壶美酒,独自斟酌没有亲朋相伴。举起酒杯邀请清幽的明月,加上我的影子正好成为三友。然而明月不知道饮酒,影子徒然随我,哪知我孤身的辛酸!世事如梦,一醉陶然,那就暂且以寒月和瘦影相伴。狂歌天地,曼舞翩跹。月儿伴我歌唱,影子随我舞零乱。趁清醒尽欢乐,沉醉后各分散。愿与月华永结忘情之游,在那浩浩的银河边再续前欢!
艺术就是充满醉意的舞。
黄山谷这段文字很有趣:“余寓居开元寺之怡思堂,坐见江山,每于此中作草,似得江山之助,然颠长史狂僧皆倚酒而通神入妙,余不饮酒忽十五年,虽欲善其事而器不利,行笔处时时蹇蹶,计遂不得复如醉时书也。”(《书自作草后》)风景再优美也不顶用了,江山也帮不了他多少忙,并不是不喝酒就不行,他缺少的是一股醉劲,没了这股醉劲,这性灵的穿透力就差多了,他感到“时时蹇蹶”的原不是笔,而在于心,因为心灵束缚的东西多了。“兴来走笔如旋风,醉后耳热心更凶。”(苏涣《怀素上人草书歌》)醉使得艺术家有了穿透力,有了无穷的创造能量,如画僧贯休所说“醉来把笔猛如虎”(《释怀素草书歌》)。山谷看来缺少的正是这种力。
中国艺术浸透了这醉意。酒和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晋代的一位名士说:“酒使人人自远”--酒使人有了超越的力量。唐代画家王墨,“性多疏野,好酒,凡欲画图障,先饮,醺酣之后,即以墨泼,或笑或吟”,醒时则不能,醉中却别有世界。
书史上记载唐代草书大家张旭每作狂草,多醉酒,酒和他的草书是联系在一起的,没有酒,几乎就没有这位伟大的书法家,所谓“张公性嗜酒,豁达无所营,皓首穷草隶,时称太湖精”。《国史补》记载:“饮酒辄草书,挥笔而大叫,以头揾水墨中而书之,天下呼为张颠。醒后自视,以为神异,不可复得。”《述书赋》说他:“酒酣不羁,逸轨神澄,回眸面壁而无全粉,挥笔而气有余。”
因酒而醉,由醉而狂,狂来甚至以头发代替毛笔,大叫大呼,其势难挡。据韩愈《送高闲人上序》的记载,这位书家,不仅因酒而醉,还有一种痴迷的精神,对大自然中的一切每观之,必专心,与自然一起跳舞:“往时旭善草书,不治他技,喜怒窘穷,忧悲、愉佚、怨恨、思慕、酣醉、无聊、不平,有动于心,必于草书焉以发之。观于物,见山水崖谷,鸟兽虫鱼、草木之花实,日月列星,风雨水火,雷霆霹雳,歌舞战斗,天地事物之变,可喜可愕,一寓于书,故旭之为书,变动犹鬼神,不可端倪,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。”
怀素也是一位醉客,他的书法成就和酒名都堪与张旭相比。李白《赠怀素草书歌》:“吾师醉后倚绳床,须臾扫尽数千张,飘风骤雨惊飒飒,落花飞雪何茫茫。起来向壁不停手,一行数字大如斗,恍恍如闻鬼神惊,时时只见龙蛇走。”戴叔伦有《怀素上人草书歌》:“楚僧怀素工草书,古法尽能新有余。神情固竦意真率,醉来为我挥健笔……”任华《怀素上人草书歌》说他:“十杯五杯不解意,百杯以后始颠狂,一颠一狂多意气,大叫数声起攘臂。”
诗善醉,艺术需要这醉意,不光因酒。我们为“常”所包围,所以,我们需要醉意。“常”是一个被理智、欲望、习惯包裹的心灵,这样的心灵“下笔如有绳”,处处有束缚,点点凭机心,玩的是技巧,走的是前人的熟门熟路。无所不在的法,控制着人,如同对待一个奴隶。所以,在艺术这“花间”我们需要这“一壶酒”,它使我们在“醉”中恢复了生命的“春”。它引着我们“人人自远”,从凡俗中腾挪开去。
在醉意中,我们开始打自己井里的水来饮了,我们总是习惯于饮别人井里的水,以这样的水滋润心田,我们的心田种的是别人的庄稼,我们收割的是和别人一样的千篇一律的谷子。然而在醉中,我忘记了别人的井在何处,忘记了跨入别人井坎的路。在饥渴中,蓦然从自己的井中汲水,原来这里也涌着甘泉。“君看古井水,万象自往还”,原来是这样令人陶然的世界。
清画家沈灏说:“騞(huò)然鼓毫,瞪目失绡,岩酣瀑呼,或臞(qú)或都,一墨大千,一点尘劫,是心所现,是佛所说。”(《画麈》)云霓就在我深心激荡,我舔毫和墨,倏然飞舞,忘眼前之笔墨,失当下之绢素。我心在沉醉中融入了画中,那岩石枯槎似乎都酣然如醉,那涧水飞瀑似乎都在向我惊呼,我就像陆龟蒙一样,似乎变成了一只忘机鸟,在无边的天宇中自由地翱翔。这一墨就是三千大千世界(空间),这一点就是无始无终的绵延(时间),时空的无限都在当下成就。“是心所现,是佛所说”,说得何等痛快!干净,利落,单纯,崇高,人们常以为以禅比诗流于玄妙空虚,以为以佛比画总有点疏阔茫然,实际上,通过沈灏这两句话,则可见禅艺相通之精髓,禅在当下,悟在平常,一点真心就是禅,些子微茫就是真,只要是本心所现,就是真,就是悟,就是禅,就是佛,就是艺。醉只是对那些可能威胁真心的罗网的逃脱,痴只是对那种思前量后的妄念的阻隔,醉翁之意不在醉,而在无念之间也!
石涛就是主张从自己井中汲水的艺术家。他在一则题兰竹的流江左久客,旧游得意处,珠帘曾卷。载酒春情,吹箫夜约,犹忆玉娇香怨。尘栖故院。叹璧人檐,梦云飞观。送绝征鸿,楚峰烟数点。“下阕是连,上阕是断;下阕是圆,上阕是缺,然圆处就是缺处,断处就是连处。送绝征鸿,楚峰烟数点。正是此意。
“断浦沉云,空山挂雨”、“小雨分山,断云笼日”、“断碧分山,空帘剩月”,等等,诗人这些刻意的创造,原都是在缺处着眼。
结 语
变化不已,运转不息,飞扬蹈厉,从容中节,这是舞的精神。舞的精神,就是要打破这寂寞的世界。在空白的世界舞出有意味的线条来。中国艺术将此化为具体的艺术创造方式,或在静穆中求飞动,或在飞动中求顿挫,或从常态中超然逸出,纵肆狂舞;或于断处缺处,追求一脉生命的清流。总之,静处就是动处,动处即起静思,动静变化,含道飞舞,以达到最畅然的生命呈现。
- 上一篇:熊猫金银币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? 2018/3/20
- 下一篇:流通纪念币收藏有窍门 2018/3/19

